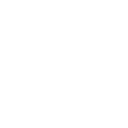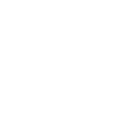伟德体育(BetVictor Sports)国际官网(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1月24日,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屹致电慰问湖北文艺工作者,指出中国文联与湖北文艺工作者勠力同心、并肩作战。身处疫情中心的武汉市文联和武汉市书法家协会、武汉青年书法家协会于1月28日在《翰墨楚风》微信公众号发出《关于举办“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夺取胜利——武汉书法篆刻网络媒体展”的通知》。《书法报》于1月29日在同名微信公众号发出《书法人在行动!“抗击疫灾,我们同在”书法创作特别征稿》的启事。2月1日,在中国书法家协会部署下,中国书法出版传媒公司旗下的《中国书法》杂志和《中国书法报》联合推出“‘防控疫情·万众一心’主题书法网络展”第一期。书法界的创作热情被迅速激发。

全国省市县各级书协,各种非官方社团,乃至于一些开设书法专业的高校,只要有微信公众号的,几乎没有不举办同类征稿和展览的。一些没有微信公众号的社团,也使用“美篇”等应用程序组织类似展览。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次网络书法展览,与本次抗击疫情一样,也是一场“总体战”“全民战”。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同一主题、同一途径(网络)在同一时段集中推出,规模前所未有,形式前所未见,传播广度也是前所未闻。 疫情仍在持续,这一形式的书法创作、展示、传播活动也仍在持续推进中。“翰墨楚风”的网络展共持续了5期,《书法报》的征稿也已刊登了4期,中国书协部署网络展5期。有的省市书协的力度更大,如江苏书协的网络展已经发布到第38辑(见其微信公众号)。疫情防控结束后,也将会有后续的相关活动继续开展,比如一些网络展延伸为线下展、部分作品进入拍卖捐赠环节乃至被公立文化机构收藏等等。
众所周知,书法最初源于文字的使用,举凡社会生活中需要文字处,便可以是书法展示的空间,由此产生了甲骨钟鼎碑刻尺牍等极为丰富的作品。宋元以后,书法在一定意义上逐渐成为精英文人享有的“专利”,主要研讨场所变成了文人们的书斋。明清以后,随着商业兴起、建筑高大、文人集团膨胀分化等社会变化,书法重新走出书斋,进入有条件的家庭以及其他生活空间。民国以来仍延续这一趋势,但同时增加了一种新形态——进入展厅,参与美术展览。随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书法展览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活动方式。当自媒体特别是微信、抖音和快手等广泛流传之后,事实上书法活动已经出现了一个崭新平台。与过去所有方式相比,它是虚拟的,但同时传播力又是超级巨大的——它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 不同的场合,对书写的要求必然会有差异。文字学家在讨论甲骨和金文时,有“正体”与“俗体”的分别,判断标准之一就是应用场合,正规场合多偏于工整,普通场合则或有草率。到南北朝、隋唐时期,这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官方碑志与庶民之间总体上存在非常巨大的差别,主要出于官刻的“元氏墓志”,整体上就显得工整有序得多。这种区别,与各自“场合”主导者的需求有密切关系。工整端严,通常是正规场合的第一要求,即便在文人占据书法主导地位的宋元时代也是如此。明清时期的庙堂、朝廷等公共场所使用的对联、匾额,总体上也遵循这一规则。
考虑到公众接受这个审美维度,强调在主要面对公众的场合对作品的字体风格进行一定的选择,表面看来可能扼制艺术家个人风格的发挥,然而实际可能正相反。通过长期训练及各种机缘养成的艺术家个人风格,在面对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完全有可能因受到各种审美需求的挑战而产生积极的变化,获得更加深入社会和历史的创造性契机。据我并不完全充分的观察,本次网络展中,有不少书法家事实上解锁了自己的许多技艺,原本较少用于创作的一些书写才华,在这个过程中被释放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有更多的艺术家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书法就有可能借助现代化的网络渠道,重新全面回到生活,汲取更加丰富的时代养料,为发展出新时代中国书法艺术的高峰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然而,要实现上述观念转化乃至付诸实践,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书法”与“写字”的关系问题。前文已经述及,书法从一开始即以文字为创造对象。而文字是记录语言和思想的工具,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有文字处必有书写。书写可能存在的独特审美功能与文字的信息记录传达功能一体共生,无法拆解。大约自汉代后期开始,专门追求“翰墨之道”的行为开始出现,文字书写不必再仅仅是为事功服务、为考课效劳,而可以供人“游手于斯”。通常认为,这是书法独立为“艺术”的表现。自此以后,历朝历代,都有若干贤哲,本乎天地之心,取会风骚之意,或以尺牍为媒介,或借碑版以驰骋,俊发灵府,妙舞霜毫,抒情写意,使笔墨成为“人”的写照。然而,即便在他们的笔下,大多数时刻,书写与信息的记录传达之间,也并不截然分离,而常常是不分彼此的。与此同时,书法史自身也在不断地梳理源流,把大量原本并不出于所谓“翰墨之道”的企图而产生的作品,纳入到书法史的长河之中,使得两者之间的区分更加模糊交织。后世大量以“翰墨之道”为追求的“创新”,其历史范本恰恰常常是这类没有明显独立的“翰墨之道”追求的作品。写字与书法,就历史来说,事实上完全是难以分割的存在。


这个现象,要求我们反过来进一步思考书法作为艺术的特性。一方面,它与其它艺术一样,有自己的历史传统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一系列技术规定,具有相对稳定的自律性,由此形成艺术的“门槛”;但另一方面,它又时刻向日常书写敞开,不断从日常书写中发现自己更加宽阔的领地和边界。人们常常认为,书法的笔墨是抽象的,因而难以表现过于具体的社会事件和人生情感。仅从笔墨上说,这是事实,你无法抽象地说某种笔墨是“悲伤”的而另一种笔墨是“欢乐”的,也无法说某种笔墨表示“庆祝”而另一种笔墨表示“诅咒”。然而,在书法中,笔墨与文字是共生的。没有文字作为先导,书法的笔墨无从生成(当代艺术不在本文议题范围,不讨论),每一种笔墨,都是在该作品所赖以产生的语言环境中生发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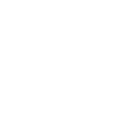

@HASHKFK